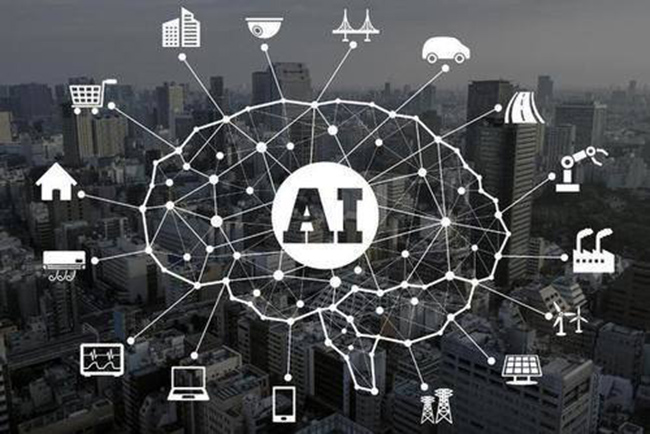“人工智能”中的“智能”盡管還不是嚴格意義上的人的智能,但作為一種隱喻,目前已被廣泛認可和接受,即認為人可以通過技術的手段使某種人工設備表現出類似于人的智能的現象或行為,即創造出某種人工的設備來完成那些類似于需要人的智能才能完成的任務。人工智能作為一種新技術,因其具有近乎無限的可能性,引起了人們無窮無盡的聯想,其中影響最大的就是對它可能失控即反過來統治支配人的種種恐懼與擔憂。
如果引入歷史的眼光來分析這一問題,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借鑒人類對另一種技術——人工體能——所經歷過的“愛恨情仇”心路歷程,來理解和釋懷我們今天對于人工智能技術的種種感受,從而尋獲一種更為合理與開通的對待人工智能的態度。
一
“人工體能”也是一種隱喻性的提法,它和人工智能一樣,都屬于一個更大的范疇:“人工能力”。我們知道,人不僅有借助自己身體形成的“自然能力”或“自身能力”,而且能通過自己制造和使用工具來延長或增強自身的能力,這一部分由人借用技術(如機器)來人工地從身體之外獲得的能力,可稱之為“人工能力”。人工智能顯然就是這里所說的人工能力之一,而比人工智能出現得更早的一種人工能力是“人工體能”,它的“人文效應史”可以作為一面鏡子為我們今天對人工智能進行評價和理解提供參照。
帶有發動機的機器是人工體能技術的典型代表,因為發動機就是將人身之外的自然力轉化為推動機器運轉的“人工動力”,使得機器不再像手工工具那樣只能靠人的肌肉提供動力。人工體能技術帶來的“動力革命”意義重大,從此人類進入了主要依靠人工體能的大機器生產的工業文明時代。人工體能技術在剛剛出現時,也引起了震動效應,無論從心理感受上,還是從支配與被支配的認知上,都有類似于今天人們面對人工智能時的反應,這樣的感受和認知被許多著名的思想家描述過。如美國技術哲學家芒福德將機器時代描述為“野蠻的新紀元”,德國學者斯賓格勒則將機器的出現與“西方的沒落”聯系在一起,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更是將以大機器為代表的現代技術的本質歸結為“座架”,馬克思則分析了工人在巨大的機器及其“瘋狂的旋轉中迸發出來”的“魔力”面前所感到的“渺小”,當然馬克思的重點是指出機器的資本主義應用才是造成許多負面效應的根源。
二
可以說,今天我們在人工智能的初級階段所形成的種種恐懼,也十分類似于當初人們面對機器時的上述感受,無非是形成的說法更加多樣化,諸如“奇點說”,或視人工智能為人類的“終結者”,此外還有“養虎為患說”“強弱易位說”“稍有不慎滿盤皆輸說”“AI將是人類的最后發明說”,等等。
之所以存在對于人工智能的恐懼,主要在于人們擔心它在未來水平和“能力”提升后會超出人的控制,當“人的智能”不如“人工智能”時,人就無法再駕馭和支配人工智能。這里且不說人工智能即使在高級階段是否能具備真正的“智能”,即使真的具備了超過人的智能,就像目前的智能計算機在記憶、計算和圖像識別能力上已經遠超于人,但我們并未感到失去了對人工智能的支配。再借鑒人的體力和人工體力的關系來看,各種機械裝置的“體能”早就遠超于人的體力,但人類并未因此認為從總體上已經不能支配人工體能技術了,更不會出現在機器使用的初級階段那樣去搗毀機器的情況了,也不會提出棄絕一切機器回到手工時代的主張。可以說經歷了初期的那些對機器的恐懼性感受和認知后,今天我們看到人類對于人工體能技術的態度日趨理性和冷靜,這無疑也是在未來的人工智能技術使用中我們有可能再度經歷的認知提升。
將來當人的一切工具性職能都被人工智能替代之后,人專司于如何使用和支配各種人工智能器具,甚至對人工智能的哪些功能需要開發哪些功能不需要開發抑或限制開發甚至禁止開發,將會達成透徹而成熟的認知,從而將“失控”的風險降到最低。人和智能機器的這種新的分工,正是保證無論多高端的人工智能器具都將受制于人的基礎。人類的主體意識在人工智能時代將和在人工體能時代一樣,必將延續和發揮下去。所以,這里存在一個如何理解“控制”的問題,控制絕不是一點失控現象也不發生,而是總體上的被人類所掌控。這里也存在對兩者評價的對稱性問題:當我們擔心由人工智能驅動的機器人會不會集體失控時,可想象一下那些由人工體能技術驅動的飛機、火車會不會集體失控?從更大的視野看,人工體能和人工智能都是人工的技術,它們是否失控的問題,也是技術與人的關系問題。
三
這種意識無疑需要從專門的視角加以“深度挖掘”才會形成。從“生活世界”中人們的直接認知來看,機器這樣的人工體能技術的使用給人帶來更多的還是有利的效用,以至于不使用機器這樣的人工體能技術,我們的許多主體性目標就不能實現,如我們就不可能有機械化作業的高效率,就不會有機動化交通工具的高速度,我們的物產就不會像今天這樣豐厚,我們能親身游歷的空間也不會像今天這樣廣闊。這里的關鍵是人對技術的“支配”地位是否在終極意義上得以保持。在機器作為人工體能技術被使用時,由于機器運轉的剛性需要(其機械性連續運轉等特性),使得人要在適應機器特點的前提下才能使用機器,如機器運轉時人就需要跟隨機器做相應的操作活動,機器才能為人生產出他所想要的產品,在直接性上就表現為機器對人的形式上的“支配”;而在最終目的上,還是人利用了機器,而非機器利用了人;或者從總體上說,人工體能技術是工具和手段,人的需要才是目的。因此從這種“日常認知”中我們更多體會到的是人對機器的控制,而不會認為是機器支配著人,否則誰還愿意使用機器?誰還樂意坐車乘機去旅行?這種“日常見解”或許比某些“深層的”哲學見解更能代表人工體能技術與人的關系的現狀,從而更能作為技術決策的根據。
甚至從剛性的操作上,人工智能時代人對技術的支配力還具有比對人工體能技術的支配力更強的一面。例如由于人工智能對機器可以實行自動控制,人就不必再固守在機器一旁,從而擺脫了跟隨機器的運動進行操作的被動性,對人尤其是對直接勞動者來說,這就是一種新的解放,一種使人更加自由的模式。
如果技術的人文效果是社會建構的話,那么人群中絕大多數的技術使用者才是建構技術效果即形成價值評價的決定性力量,當他們從先進技術的使用中獲得好處時,他們對技術的贊同對于技術發展前景才更具有意義。所以,從這樣的視角去看,人工智能未來的命運不會由少數悲觀的“預言家”來決定,當其有效合理的應用確能給公眾帶來實在的好處時,如同今天的人工體能技術已經做到的那樣,人工智能的發展就會獲得一種來自社會需要的強大推動。說到底,人類創造的技術之于人的終極效應,取決于人自己,只要人類作為一個整體是理性的,我們就不用擔心人造物(包括人工智能)毀滅人類的那一天會到來。